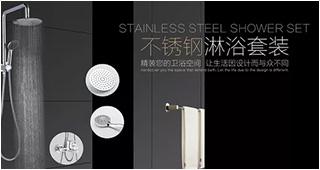作者:廖榕光 吴达生
吴国乡的灵柩一路穿越千山万水,当年九月回归故乡南安,仑美吴氏举族哀悼,早已搭起灵棚,迎接灵柩安放,又延请安溪县名刹高僧就家建起“三宝坛”,开光请忏,为吴国乡“牵藏”“做功德”,超度亡灵。泉州知府、南安知县及地方乡贤达人,纷纷前来吊奠,极尽哀荣。时值深秋,梧桐和柿树的树叶,伴随着“做功德”的仪式中深沉哀怨的“嗳仔”声在风中飘零,更添悲凉气氛。乡亲们痛失英才,灵前致祭都泣不成声。“七昼夜”功德圆满,灵棚拆卸,吴国乡灵柩暂厝,择吉安葬。而吴国乡的神主牌位则请入祖厝神主龛安位。
毕竟吴国乡生前在家乡德才兼备,出仕又政声斐然,遐迩闻名,丧礼完毕仍有不少远方人士前来吊奠,一律接入奉祀吴国乡神主的祖厅焚香鞠躬,宾客发现龛里供着的吴国乡神主,旁边还并列供着一位神主,细看其文曰:故先妣号柔婉延陵吴门郑氏孺人神位。心生诧异,吴国乡夫人陈氏现仍健在,四子一女皆陈氏所生,从来未听过吴国乡有先室呀!茶叙之间,有人悄悄向吴氏宗亲询问,宗亲告之:吴大人确有郑氏先室,只是郑氏未婚而卒,吴家依礼迎娶其神主为正室。来宾这一问,引出了一段早已尘封的爱情故事。
话说吴国乡当年才15岁就中秀才,这是吴氏族中脱颖而出的少年才俊,父母很是高兴,送其到80里外的丰州南安县学继续深造,每月必回家一次拜望双亲。国乡自幼节俭,为省船资,他不从珠渊渡头搭船,而是步行到溪美渡头搭乘美林渡船到丰州九日山下登陆。回程也是从丰州乘船至溪美下船走陆路。仑尾到溪美有30里路程,须路过杨梅岭、莲塘、崎口等地。有一次走到崎口,口渴难当,看见路旁有户农家,乃上前叩门讨杯茶水。日近巳时,主人家劳作未归,一位姑娘应声出门。国乡上前拱手施礼道:“小生是位生员,在县学读书,今回家路过贵地,因口渴难当,斗胆敲门讨杯茶水止渴,感恩不尽”。那姑娘十分善良,连声说道:“先生休得客气,些小茶水,举手之劳,何恩之有”。说毕转身回屋,取出茶壶茶杯,泡着满满一壶乌龙茶,也是口渴太甚之故,一杯入口满齿生香。国乡连声“谢谢姑娘芳茗”。那姑娘笑吟吟地说道:“既是读书于此经过,先生如不嫌弃,他日路过,再来饮茶”。吴国乡再次称谢,拱手作别。
谁也不曾想到,这偶遇的因缘牵出了一段哀怨凄美的姻缘。
原来那姑娘姓郑,出身中等农户,父亲读过几年私塾,虽未成功名,却知书达礼,在乡里也算个文人,家教甚严,家风淳朴。姑娘名叫“月娘”,当时年已二八(十六岁),正是豆蔻年华。她见吴国乡少年英俊,又是言行举止规矩矩的秀才,萌生爱慕之心,常常在空闲时在门口痴痴远望,只盼那位少年书生再来饮茶。也是合该有缘分,有一次月娘正在门口怅望,恰巧国乡又从门口经过,此次郑月娘首先开口曰:“这位先生又要回家了吗?不妨喝茶小歇,再走未迟”。国乡见姑娘诚意,也不推却,就在门外石椅坐下,月娘依然泡出一壶香茗,一旁侍立看国乡喝茶。前已见了一面,月娘胆子较大些了,便道:“敢问先生何方人氏,尊姓大名。如肯赐教,日后相遇也好有个称呼”。国乡如实相告,“小生姓吴名国乡,家住廿七都仑尾乡”。少倾,吴国乡告辞继续上路,月娘默默注目国乡背影,心中怅然若失。
却说那郑父本是细心之人,发现女儿沉默寡言,有时眉头不展,做事心不在焉,感到不正常,乃盘问道:“女儿近来食欲减少,面色无光,有何心事尽管与阿爸阿母禀明。如是有病,该请个郎中来问诊才是”。女儿不敢当父亲明讲,乃将与吴生相遇之事及暗恋之情如实禀告母亲。郑母遂与丈夫相议,郑父道,吴国乡是仑美才子,名声附近都知道的,既有此机遇,待他再过家门,我与他见面就是。郑母转告女儿:“汝父吩咐,这几日留神注意,吴国乡如过家门,请他进来,父亲有话问他”。
果然不日国乡又路过郑家门口,郑月娘欣喜至极,满面笑容对国乡道:“吴先生辛苦了。我父亲请汝入内饮茶”。国乡说:“多有叨扰贵府,却未曾向你父亲面谢,该当进见”。乃随郑月娘进入前厅,郑父起身示意国乡西边坐下,见他气宇轩昂,果然不凡之辈。先问些家在何乡,现学业如何之类,国乡一一禀告。又说:“求学之间屡从贵府门前路过,小憩时令爱赐茶多有叨扰,从未对年伯当面称谢,非常抱歉”。说罢起身作揖。郑父也起身还礼,连说不用客气,又问是否婚配。吴国乡禀道:“初得生员资格,有意再进取功名,待乡试得中再议婚事不迟”。郑父又开言:“以汝之才当以天下为己任,先求功名后求家室顺理成章啊。现在吾家小女有爱慕之心,汝若不嫌弃,可以禀告你父亲,前来议婚。我想这也是三生注定好事,望勿推辞”。吴国乡拱手回话:“年伯不弃,小生已是不胜荣幸,岂敢推辞。惟婚姻大事须父母做主,我当即禀明双亲,依礼而行”。一阵茶叙之后,国乡告辞。月娘已在屏风后听得清清楚楚,心中欢喜。郑父叫声女儿送客,月娘早已笑吟吟走出大厅,送吴生出门上路。
国乡回家即将郑家所提之事禀明父亲,父亲道:“崎口距我家不远,既有此等好事,我就不用媒妁之言了,待我委托有崎口亲戚的乡党调查、暗访一下,郑家若家风端正,就可定夺”。不日,暗访探来消息,郑家也是耕读之家,虽然清贫,却安分守纪,和睦乡亲,乡里口碑很好。吴父听了大喜,择吉日邀宗长伯叔连国乡一行6人,亲到崎口郑府提亲。这本是瓜熟蒂落之事,又兼双方都是书香门第,见面后都是说些客套话,并无一般人议亲时关于“六仪”聘礼数量、程序讨价还价之争执。之后,吴父又择吉日送聘,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。时在乾隆三十九年春夏之交,吴国乡年已二十,郑月娘一十六岁。
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古代封建社会,吴郑这门亲事算是“半自主”了,实属一段佳话。偏那郑氏月娘是个多情种,与吴国乡一见钟情就萌生爱意,议聘成功后更是朝思暮想,恨不得天天见面。那吴国乡有时半月回家一趟,功课忙时也曾一个多月才回家一次,每次来回都先经郑家,月娘缱绻情深,默默含情迎送,她生性言语不多,无恨情恩郁郁胸中,日久生病。乾隆四十年冬,一场伤寒起病,过春节后未见好转,越病越深,这可惊动了吴郑两家。郑父曾提议依例俗请吴家迎娶去“冲喜”,也许会好转。吴父答道:“‘冲喜’之说纯属无稽之谈,不可迷信。为今之计急请各地名医会诊,靡资我吴家全责承担”,遂派人泉州、安溪各地寻访各路名医会诊,指望春暖花开,病势慢慢转安。岂料心病无药,名医也无力回天。暑天,县学放假,吴国乡来郑家在月娘身旁朝夕守候。一日,月娘执国乡之手细声呜咽叫道:“吴郎,妾得许配汝身,天遂人意,别无他求了。知你功名未就,未敢越雷池半步,‘冲喜’之说非我所愿。我生为吴家人,死为吴家媳。死后得与夫君同穴,我愿足矣!”声声细细、悲悲切切,泣不成声。吴国乡早已泪满两腮,只是劝慰贤妻不必过分伤悲,容再换良医来诊,切莫胡思乱想,安心养病。月娘又强振精神告道:“真病无药,妾自知气数已尽,有郎君在病榻相送,虽未同衾,死亦无憾”。说毕,一缕芳魂冉冉飘去,撒手归西了。吴国乡跪倒榻前哀号,竟至昏厥。
郑家小姐未过门身逝,依礼急报吴家。吴家派宗长伯叔男女眷属一行到崎口,按崎口风俗办理月娘后事,收埋停当。三年之后,吴家迎娶郑月娘神主过门,于是有了前文所述吴国乡神主旁的“先妣”神主牌位。
吴父心想,既然娶了郑月娘神主过门,国乡有了先室,且三年礼尽,“续弦”再娶是名正言顺的,毕竟抱孙和儿子功名同样重要。此番由不得国乡主意了,托媒说亲,果然寻得安溪县城陈家女儿,门当户对,吴父十分喜欢,叫来国乡将详情相告,国乡也不敢再坚持什么乡试中举再议婚事的原则了,只称“谨遵父命”。
陈氏名熙娘,依礼成为吴国乡继室,共生四男一女,长子及女儿均不幸早逝。吴国乡逝世后,陈氏含辛茹苦抚养二子武诣、三子武谐、四子武谈三人成长,先后中了秀才,都不愿出仕做官,不参加乡试,躬耕田亩,耕读传家。天佑忠良之裔,吴家一门后续人丁兴旺,勤朴家风世代传承。陈熙娘于道光丙戌年逝世,享寿65岁。

(吴家族谱关于吴国乡夫妻生卒及墓葬的记载)
道光丙申年(公元1836年),陈熙娘“拾骸”,遗骨拾入“皇金”,吴武诣兄弟三人择吉地为父母筑合圹大墓,吴国乡“皇金”、郑月娘衣裳首饰、陈熙娘“皇金”三圹同穴安葬,入土为安。此时,距郑月娘乾隆丙申年逝世已经整整一轮甲子了。郑月娘生未与吴国乡同衾,死后60年终与吴国乡同穴,遂其所愿,可惜只是在夜台与夫君相会了。正是:
生未同衾,死终同穴。
生死夫妻,千秋传说。
(《吴国乡传奇》全集至此续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