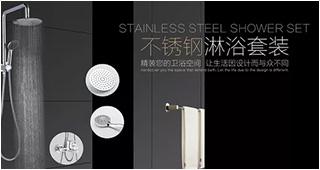作者:廖榕光 吴达生
乾隆五十九年夏秋之交,大宁县又出了一条人命案。九月的一天,正逢大宁赶集,斯时农事已毕,小小的县城,街上商贾、农樵熙熙攘攘,摩肩接踵。城东小街,靠近薪炭集市,樵夫负薪叫卖,特别拥挤。此时,一位樵夫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松枝干薪匆匆赶集,不料在人多拥挤之处受行人挤蹭,后头柴捆突然脱落,挑柴的尖头扁担因惯性力霎时间飞起弹向前方,正好击中一位行人的囟门脑盖,那人应声倒下,鲜血从脑盖喷出,顿时一命呜呼。
东门闹市出了人命,马上有地保控制卖薪樵夫,更有热心人到县堂击鼓报案。此时恰逢吴国乡去隰州述职,县丞一面差人速往隰州州衙报禀老爷,一面领主薄、衙役、仵作等人赶往现场。仵作验明尸首,系钝器击伤囟门,伤口二寸,出血甚多,业已毙命。主薄记录在案。县丞初审那樵夫,樵夫供认伤害人命,画押在案。于是,县丞命取棺木将死者尸首入殓,樵夫收监听审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吴国乡回县堂审阅了案卷,心想,此系偶发事件,并非有意杀伤人命,与图谋不轨故意行凶杀人者性质不同,心存怜悯,立即提堂亲审。案犯押到公堂,吴国乡发问:“下跪案犯是何姓名,家住何方?你与死者有何仇怨,竟起杀人之念?”这问话明明是向那人提醒。那人禀告道:“小民姓郑,单名平。家住东门外岭下乡,世以农樵为业。我与死者并无仇恨。他确是被小民所害”。吴大人又问:“你可知蓄意行凶杀人是大罪,朝廷律例规定严惩?”那郑平禀道:“回老爷,自古杀人偿命,今日我无话可说”。吴国乡思忖,此人真是头脑只有一条筋,老爷分明怜悯汝无端受罪,你却脑不开窍,简直是冥顽不化,口供记录在案,无可救药了。长叹一声,“罢罢罢”!叫主薄认真与他核对口供,画押归档。
那无辜死者是秀才出身,且又是独子,家人数次含泪告状,请求早日判决郑平死刑,务必杀人偿命。吴国乡耐心安抚逝者家属:“依照大清律例,本官已将案情审结上报,量刑由知州、府尹裁定,生杀大权在上司”。
不料此案报到隰州,知州审核后即令判处死刑,公事下达到大宁,已是腊月。吴国乡含泪拟了判决文书报批,上司也快,批示“斩立决”。时已届年关,死刑犯不得越冬,必在年内执行。吴国乡命为朝廷命官,王命在神不敢怠慢,吩咐给死囚郑平吃了“长生面”,即押赴刑场,与上司派来监斩官一起监斩。眼看行刑刽子手鬼头刀一挥,血淋淋的人头落地。吴国乡一时头晕目眩,几欲昏厥,一言不发,上轿回衙。
监斩归来,吴国乡回想赴任之际母亲的耽忧,如今枉杀无辜,果然被母亲不幸言中,痛切万分。想起当年在母亲面前指天发誓,如今竟违背誓言,亲自监斩一位罪不该死的犯人,与枉杀无辜何异!不断深深自责,整日忧心忡忡,不能自拔。多少夜辗转反侧,认为非全节尽孝不能解脱,勉强过了新年,立遗书安排后事,诀别娇妻陈氏,千恩万谢拜托抚养四男一女成人。写毕吞金自尽,其时正是乾隆六十年即公元1795年二月初二日,享年四十一岁。吴公归天之时正是辰时,春雷大震,鸣声持久,大雨滂沱,令人惊骇不已。大宁百姓当日就得知吴大人清早逝世,纷纷争传“天鼓大鸣,是迎接吴大人忠魂升天也”!
吴国乡任知县二年,身后竟无积蓄,无力运柩还乡。隰州知州报奏朝廷,皇上悯其忠勤廉节,准拨山西库银赐葬,晓谕灵柩还乡之所经州县、沿途驿站好生接待,军民为灵柩过境提供方便。灵柩出了山西,取京杭大运河水路南下,至杭州弃舟登陆,换灵輀上路。杭州知府刘肇基早已知情,拦车设坛路祭,并撰挽诗曰:
共说梅英日映魁,人琴一去未曾回。
才名首出南宫選,品望高儗月旦载。
帝里无家成蝶梦,灵輀有泪动猿哀。
忠魂驾鹤归何处,应与修文入夜台。
(未完待续。请看下期《吴国乡传奇之七》)